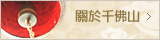- 文:若知出處:雲語書摘期數:412期2025年8月
雲公老禪師明示:「要明心見性,先要修心養性。」而修心養性,本來就是出家人的日常功課,該從何下手?自然是要從照見自我下手。
雲語書摘 結夏安居何所為
/若知
佛門子弟結夏安居何所為?不外以明心見性為標的。所有一切讀經、拜經、拜懺、行法、止觀、 參禪等,不外導向提昇自我、明心見性。古德說:「千經萬論 衹為明心。」因為心是萬法之源,「心生種種法生,心滅種種法滅」,《大乘本生心地觀經》更說:「三界之中,以心為主;能觀心者,究竟解脫,不能觀者,究竟沉淪。」雲公老禪師明示:「要明心見性,先要修心養性。」而修心養性,本來就是出家人的日常功課,該從何下手?自然是要從照見自我下手。
雲公上人畢生的心地發明是〈千佛山止觀法門〉。〈千佛山止觀法門〉最早叫「禪那輔行法門」,發表於西元1980(民國69)年《佛印月刊》第85期與86期。「禪那輔行法門」梵文是〈阿舍那僧涅陀耶他摩〉,意思是「在靜態的勝境中發現什麼!」
老禪師特別介紹說:「本法門乃是輔助運用思想,發揮智慧的一種方法,適合於任何的宗派,任何的行門。舉凡學佛行者,甚至教外人士,有意修心養性的任何仁者,衹要依之修持,詳加揣摩,必能獲取深厚的利益。」
何謂「禪那輔行法」?所謂「禪那」,是禪那波羅蜜的省稱。禪那在梵文中有四含義,舊譯有三:棄惡、思惟修、功德叢林; 新譯則是靜慮,通常梵文的涵義相當豐富,比方「波羅蜜」(波羅蜜是三藏大師鳩摩羅什的翻譯,玄奘大師翻波羅蜜多,多衹是梵文pāramitā一字的尾音,沒任何意思),就有「事究竟、到彼岸、度無極」等義,加上雲公老禪師給以新義「方法」,就可套用體、用、相、境去解釋佛法的名詞,所以梵文詞彙的含義相當豐富,不像我們中文的形音義都是單一(一字一音一義)的特別。
「禪那」也是,從修行的先決條件「棄惡」開始,說明本體條件的重要,《楞嚴經》更提出四個清淨明誨,是修行禪那的入門要領(解析於後)。
禪那修行的方法是「思惟修」,說明了其「用」的性質;「靜慮」雖也是種方法,但以其呈現「外靜內動」的現象來說,就是一種「相」; 而「功德叢林」呢?正是「禪那」完成的結果,也就是「境」;所以說梵文的義涵很豐盛,常常一個詞的涵義就具足了體用相境的全部,而且四者之間相涵相攝,說一兼有其他三者,好比說體,其中也有用、相、境,餘類推,它不是單純的意思,含攝意蘊豐富。
老禪師有句名言:「一個完整的佛法,必須包括體、用、相、境四個內涵。」
先說明一下,禪那與禪定的內涵及差異;禪那的內涵是禪觀,所以有靜慮、思惟修的含意,有觀照的自我要求──棄惡,有完成修養的目標──功德叢林;具有覺照的工夫,所以稱得上是禪門修持明心見性的工夫。禪定講求的是定的境界,老禪師說「定是不亂」,從三昧ㄇㄛˋ(正受)開始,到三摩地(正定),都必須制心一處,入一境性,所以很容易進入四禪、八定的境界,四禪定是色界受報區塊,四空定是無色界受報區塊;學佛的目標在於出離輪迴受報,既知「三界之中,以心為主;能觀心者,究竟解脫,不能觀者,究竟沉淪。」所以禪定不能執著,必須能入也能出,發增上菩提心,追求了義,探究般若波羅蜜的究竟空義,無智亦無得,以無所得故,菩提薩埵,成就無所得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修禪定為什麼要「棄惡”?我們都知道教有明訓,戒經中說:「諸惡莫作,眾善奉行,自淨其意,是諸佛教!」「棄惡」是學佛的起步,也是成佛的基因,「棄惡」基本的認識就是不傷害他人,自然於自己也不會造成傷害;普賢菩薩的〈淨行品〉提到:「結跏趺坐,當願眾生,善心堅固,至不動地。」不動地是八地菩薩位,也是等佛覺位(佛鄰位)的開始,可見「善法」是思惟修中的基本要求。
《金剛經》第二十三品的經文提到:「復次,須菩提!是法平等,無有高下,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;以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,修一切善法,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!所言善法者,如來說即非善法,是名善法。」原來善法具平等義,無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的差別相;如果待人能如己,是不是就免除了傷害,於法就呈現了圓融。而且善法也不能執著、強調,一執著就成了非善,執著善即是非善,所以佛說:「所言善法者,如來說即非善法,是名善法」。
禪宗公認有部經很重要——《楞嚴經》,全名是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,經中提出禪修要合乎四個〈清淨明誨〉,應是禪修行人首先要建立的正知正見。禪坐如何才能清淨?禪坐如何才是依教如法?禪坐如何避免走火入魔?必須先認識思惟修的四個〈清淨明誨〉,也就是打坐的四個清淨條件。卷六經文中說:
「佛告阿難!汝常聞我毗奈耶(律學)中,宣說修行三決定義:所謂攝心為戒,因戒生定,因定發慧,是則名為三無漏學。
阿難!云何攝心,我名為戒?若諸世界六道眾生,其心不婬,則不隨其生死相續。汝修三昧,本出塵勞,婬心不除,塵不可出;縱有多智,禪定現前,如不斷婬,必落魔道;上品魔王,中品魔民,下品魔女。彼等諸魔,亦有徒眾,各各自謂成無上道;我滅度後,末法之中,多此魔民,熾盛世間,廣行貪婬,為善知識;令諸眾生,落愛見坑,失菩提路。汝教世人,修三摩地,先斷心婬;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。」
「阿難!又諸世界六道眾生,其心不殺,則不隨其生死相續。汝修三昧,本出塵勞,殺心不除,塵不可出;縱有多智,禪定現前,如不斷殺,必落神道。上品之人為大力鬼,中品則為飛行夜叉、諸鬼帥等,下品當為地行羅刹;彼諸鬼神,亦有徒眾,各各自謂成無上道;我滅度後,末法之中,多此鬼神,熾盛世間,自言食肉,得菩提路。
阿難!我令比丘,食五淨肉,此肉皆我神力化生,本無命根;汝婆羅門,地多蒸濕,加以沙石,草菜不生,我以大悲神力所加,因大慈悲,假名為肉,汝得其味;奈何如來滅度之後,食眾生肉,名為釋子?汝等當知,是食肉人,縱得心開,似三摩地,皆大羅剎,報終必沉,生死苦海,非佛弟子。如是之人,相殺相吞,相食未已;云何是人,得出三界?汝教世人,修三摩地,次斷殺生;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二決定清淨明誨。」
「阿難!又復世界,六道眾生,其心不偷,則不隨其生死相續。汝修三昧,本出塵勞,偷心不除,塵不可出;縱有多智,禪定現前,如不斷偷,必落邪道。上品精靈,中品妖魅,下品邪人,諸魅所著;彼等群邪,亦有徒眾,各各自謂成無上道。我滅度後,末法之中,多此妖邪,熾盛世間;潛匿奸欺,稱善知識,各自謂已得上人法,眩惑無識,恐令失心,所過之處,其家耗散。我教比丘循方乞食,令其捨貪,成菩提道。諸比丘等不自熟食,寄於殘生,旅泊三界,示一往還,去已無返(須陀洹―見惑已盡,入流或逆生死之流;斯陀含―一來,已斷欲界九地思惑前六品,餘後三品思惑,尚須於人間或天上受生一次;阿那含―不來或不還,已斷盡欲惑後三品思惑,不再來欲界,受生於色界與無色界;阿羅漢―斷盡一切見惑思惑之聖者,名應供、不生、殺賊,已入無學位)。
云何賊人,假我衣服,裨販如來,造種種業?皆言佛法,卻非出家,具戒比丘,為小乘道;由是遺誤無量眾生,墮無間獄。……。汝教世人修三摩地,後斷偷盜,是名如來先佛世尊,第三決定清淨明誨。」
「阿難!如是世界六道眾生,雖則身心無殺盜婬,三行已圓,若大妄語,即三摩地不得清淨,成愛見魔,失如來種;所謂未得謂得,未證言證,或求世間尊勝第一,謂前人言,我今已得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道,辟支佛乘,十地地前諸位菩薩,求彼禮懺,貪其供養,是一顛迦(阿顛迦,不善之心),銷滅佛種;如人以刀斷多羅木(貝多羅樹,葉大很硬,落地撿拾可書寫文字,然此樹用刀破皮即死)。佛記是人,永殞善根,無復知見,沉三苦海,不成三昧。
我滅度後,敕諸菩薩及阿羅漢,應身生彼末法之中,作種種形,度諸輪轉;或作沙門、白衣居士、人王宰官、童男童女,如是乃至婬女寡婦、奸偷屠販,與其同事,稱讚佛乘,令其身心入三摩地,終不自言,我真菩薩、真阿羅漢,泄佛密因,輕言末學;唯除命終,陰有遺付;云何是人惑亂眾生,成大妄語?汝教世人,修三摩地,後復斷除諸大妄語。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四決定清淨明誨。」
所以禪那的修養,是要運用「思惟修」的方法,先察覺返照,看見主人翁,轉化調適,察覺到自己的缺點,提昇自己的修養,成為實際的力用,如使五根成為五力的效益。
老禪師曾說:「禪,運用思想而通達理論上的經驗;發揮智慧而完成事實上的篤行;是一種從心性上著手的上乘功夫,它可以使行者脫胎換骨。」所以轉變為自己的力量就是一種修養,這種修養是從平常修行中一點一點慢慢累積起來的, 這是個基本關鍵性的問題;絕不是說,我修禪定,盤著腿在那個地方就定下來,定下來做什麼?禪宗有一句話:你定下來,最後衹會像木頭、石頭。有道是:「坐不思惟,無異土地公!」
禪修不衹是盤著腿,坐在那個地方;真正的禪修是注重調理內心的世界(調理內心世界 ── 即從事五蘊的認識與調理),成為一種修養。讓你面對不管是怎麼亂的現實,你心內都能夠不亂,都能心平氣和的去思考;因為禪定本身就是運用思想、發揮智慧的。換句話說,禪修必須有禪觀覺照的功能,不是冥想,不落空亡;也就是禪修行者除了修禪定不亂,還要修覺觀,若不如此,就成了外道禪。
一般說禪的宗旨在明心見性,如何心明性現?當然還是在於自我調理的工夫和修養,衹要方向正確,工夫日深,水到渠成,自然水清石現;因為頓悟來自漸修,不假他力,也因此,老禪師才說:「欲明心見性,先須修心養性!」古德說:「千經萬論衹為明心。」《心地觀經》:「能觀心者,究竟解脫,不能觀者,究竟沉淪。」《華嚴經》:「心如工畫師,能畫諸世間,五蘊悉從生,無法而不造。」、「若人欲了知,三世一切佛。應觀法界性,一切唯心造。」可見學佛的宗旨即在明心,而心就是我們的五蘊。
至於如何明照自己,調理自己的內心世界呢?須於五蘊詳加認知和修養:
色蘊起 ── 根塵、能所相應,色塵緣境是誘因,心色相應,色蘊形成;要發現誘因所在,能否認清內容?老禪師提醒:「順境隨它去,逆境好修行。」誘因要辨認清楚,若是順境,該如何清淨?若是逆境,如何取捨、面對?要靠平常五蘊調適的工夫,想行間隔夠,能做到覺照,才能諸業隨緣了,不再造新殃!
受蘊生 ── 生起之剎那,明覺順受與逆受之分野,順受捨之,逆受(煩惱)提起,面對去認識(轉想為非想);以及能做到受蘊的改變,想行識就有轉機。
想蘊轉 ── 感性的想,會在事的知識經驗上計較、執著上打轉;理性的想,則陷在理的知識經驗的認知所形成的計較、執著上打轉,此皆不外自我意識(老禪師曾說:理性的知識經驗有時是以別人的知識經驗為知識經驗,還是自我意識。)所以要轉想為非想,去衡量其得失與利害,再作修正。
最理想的結果是:衹有饒益,沒有傷害。(即唯識學提到的證自證)
行蘊動 ── 若處於分別、計較、執著,有四相(人我對立),就會生出造作行為;若已做千佛山五蘊調適―─止觀的修養,此時行蘊尚未表現於外,則還有轉圜的空間,(所以說想行間隔越大,想的變化和修養就會越好。)須知到此還是內在的行相,非外在之行為;如果透過身口有所作為,不盡理想,則還是有為法,還是非想的層次;所以老禪師提出:「法義是行相的準則,生死是道業的依歸。」一回生,二回熟,省思的內涵、取捨的考量,會因為自己慈悲喜捨心境的開發,而得到調整與改變;到最後(識)呈現的結果,對人對己,必須衹有饒益沒有傷害, 才算圓滿。
識蘊成 ── 識是分別與結果。從最先的分別開始,直到能做到了別。但不夠,不管理性的或感性的,這時都還是自我意識,必須能夠轉識成智,跳出自我意識(泯四相),才不會有傷害的後遺症。但要知道:「五蘊是一氣呵成的」,快得不得了,老禪師說:「五蘊的一次變化過程,就是一個意念的生滅現象。」《仁王護國經》中說:「一念有九十刹那,一刹那有九百個生滅。」所以,老禪師教我們在想、行之間要建立起間隔的修養,而且說,想行的間隔越大,效益就越好,缺失就越少。實在是了不起的心地發明,因為這就是一種經修養而得的「明心見性」的工夫,照見自我清清楚楚,而且自我驗證,所作要完全是饒益,沒有毀損。老禪師說禪是即身成就的法門;禪那思惟修如何開發自心覺悟的能力和智慧,是個重要的課題。
《金剛經》的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便是個無相的課題,禪門有言:「著相修行千萬劫,離相修行刹那間。」佛陀說,他經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,悉皆供養承事,無空過者,但皆不被諸佛授記,直到燃燈佛的時代,能出過一切諸行,以平等心不捨一眾生,以平等心持清淨戒,以行平等心具足六波羅蜜,才得到燃燈佛的授記(見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):汝於來世,當得作佛,號釋迦牟尼。
老和尚曾明諭:※ 禪行者(作思惟修內觀的行者)不是把境界提得高高的,就表示他有了深功夫、妙道行;而是一切來自平常時的心念;意識變化中,抓住了,與生死有份;錯過了,衹是遊戲時辰。 (《思路》)
※ 禪行者的心意識不是往裡窮鑽,而是如藏竹中的鐵條,必須一節一節的打通,直到沒有了阻障為止。
所以禪門稱身心為五蘊宅,達摩祖師就常引經典說:五蘊窟宅是名禪院,內照開解即大乘門。願與大家共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