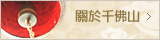- 文:鍾文音出處:菩提叢林沉思期數:412期2025年8月
西行取經是他前半生的座標,翻譯原典則成了他後半生的全部。
菩提叢林沉思 略述玄奘大師的譯經世界(上)
/鍾文音
雲遊僧玄奘法師的書房除了經書還是經書。
西行取經是他前半生的座標,翻譯原典則成了他後半生的全部。
佛是真語者,實語者。
翻譯者小心翼翼,玄奘法師翻譯經書深知必須亦步亦趨地將原典重現。他一一比對過他向來極為尊崇的鳩摩羅什尊者的各種譯本,他讚歎博通漢文與梵文的羅什尊者的譯本,能將艱澀的佛典變得有如文學詩詞歌賦般的「優美」,但他想這樣有沒有能將使讀經者浸潤文字相,而忘了本心本意?
羅什尊者對翻譯的理想是將梵文轉譯能完整和漢文疊合,認為羅什尊者的翻譯是以意譯趨近,不是逐字逐句,而是消化過的再創作。
為了讓在地讀者更容易接納梵文的在地化,所以羅什尊者選擇的漢文是當時比較被接受的風格文字。他運用佛法的善巧,只為了能讓佛法更廣傳更深入生活。於是他捨梵文的逐字翻譯,避免拗口。而玄奘法師卻不走這條意譯之路,他選擇寧可拗口也要貼合原意的文字。
他戰戰兢兢,將原典原意忠實呈現,這是翻譯者的使命。
他和當年的繁華長安周邊著迷於香禪詩等附佛者是完全不同的。
他覺得附魔容易辨識,附佛有佛依附有時反而難以區分。
他為人極簡,近二十年雲遊,除了佛經佛像佛物,其餘一概沒興趣。
但他不反對文人雅士將佛納入美學的一種禪生活,佛法突然時尚起來。文人雅士相繼習禪修法,焚香禮佛,玩香是儀式,詩、禪、香合體,詠香詩禪意詩,道場獨坐,一瓶秋水一爐香。「晨起對爐香,道經尋兩卷。晚坐拂琴塵,紅燎爐香竹葉春。」
香隨風飄送到他的鼻息,他打了一個靈魂似的噴嚏。《維摩詰經》天女散花、請飯香土,人物鮮活,想像奇迥,富於文學趣味。用淺近的方法引生大眾的信仰,是大乘經典的一大特色。
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學士最愛清談與《維摩詰經》,六朝志怪作品深受《維摩詰經》中佛教教義、文學手法之影響,大量反映惡報、地獄等場面。
僧肇讀《道德經》時發出 「美則美矣,然期棲神冥累之方,猶未盡善也」之感嘆,直到後來他讀到《維摩詰經》,頓時決定出家。
身如泡沫亦如風,刀割香塗共一空。宴坐世間觀此理,維摩雖病有神通。
「又由八相,能遍了知,遍了知故,除諸過患,當知是名,極善清淨,離增上慢,無我真智。又於此中,已滅壞故,滅壞法故,說名無常。諸業煩惱所集成故,說名有為。
由昔願力所集成故,名思所造。
從自種子現在外緣所集成故,說名緣生。於未來世衰老法故,說名盡法。死歿法故,說名歿法。未老死來為疾病等種種災橫所逼惱故,名破壞法。由依現量,能離欲故,能斷滅故,名於現法,得離欲法及以滅法。當知此中,除離欲法及以滅法,由所餘相,略觀三世所有過患,由所除相,觀彼出離。若由如是,過患出離,遍知彼識,名善遍知:名諸法印。即此法印,隨論道理,法王所造,於諸聖身,不為惱害。
每個人都質地不同,並非人人都是開悟的料,雖佛說人人有佛性,但佛性被遮掩者眾。
他從譯經院的窗外聞到了長安空氣飄盪的奇香,香塵繞樑,香客紛紛。
唐朝貿易發達的長安,域外絡繹於途的貢品繁多,在太宗高宗大內焚的香更是極品。沉香混著塵氣,歌坊鶯鶯燕燕的脂粉灑落市街,飄揚空氣中。走進譯場的人先前去了哪裡,吃了甚麼東西,身體的氣息都會標誌出來,也都難逃玄奘法師的法眼。
名香鬥豔,連菩薩也香氣十足,佛殿與案上燃香處處,銀薰香球與供佛蓮花香座都讓修行者動了凡心。
唯獨玄奘法師如如不動。
玄奘法師告誡譯經院的弟子們切莫逐香,鼻息奢華,日久會麻痺感官。行香客與坐夏僧,雙草履和一紗燈。秋寺行香去,春城拜表還。持香爐繞行,入廟焚香拜。祀天帝靈香,直達天聽,祈仙降臨。
香餅香丸,沉香、棋楠飄過,混著印度的豔香,聞到味道就知道剛剛穿行大街而過的是印度人。
印度,已是前世。雲遊,已成夢中。
貞觀十九年五月二日,距離他結束五萬里的行程只有三個月,他已經打開梵本,正式開始翻譯佛典。
從此他的一生沒有一刻離開過在茲念茲的翻譯之事,彷彿西行取經的淚水與汗水早已拓印在經本裡,無能抹滅,只能延續。
翻譯院直屬國家,他喜歡稱院為場,院太學術太正式,場則庶民,是道場。翻譯經典用的道場,譯場親切,就像他希望把經典種在人間土地,開出智慧花來。經典是光,沒有這光指引,所有的六度萬行都將無所依歸,無法生出根來。
能所相對,能所互依,取經之大能已完成,譯場之大所也初立,此心之大願已實踐,萬事皆備,只欠東風,找出能協助他翻譯志業的有緣有能的弟子們。好的上師也需要優秀的弟子,互相成全。
當時玄奘法師是邊看經典邊口述,且翻譯的同時,兼具講經、辯經,一問一答,引導經義。從印度歸返長安後,他就在慈恩寺內潛心譯經,沉思著該如何進行翻譯佛典之事,深入了解翻譯史上著名譯場的制度與譯文特色。
迦葉摩騰、竺法蘭在漢明帝時開始翻譯《四十二章經》,此是最早的翻譯。佛典口授者與筆譯者常常無法融通,因當時梵經匱乏,譯經仰賴的多是由大師口誦,卻無原典可以對照。
加上當時人力財力不足,於是最初佛經的譯本多是單卷或字體較少的小本經書,像最初傳入中土的四十二章經。
西元二、三世紀的譯師中,安息國的安世高,月支國的支婁迦讖,康居國的康僧鎧、康僧會,月支人竺法護。不少聲聞乘和大乘的經文被翻譯為漢文。限於各種條件,還未能有計劃、有系統地翻譯,此時所翻譯的經書很少是全譯本,而翻譯文體也還沒確立。
直到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,公元379年,道安大師在長安五重塔寺設立譯場,請來西域沙門僧伽提婆譯出阿含等小乘論書,這使長安城自此成為北方譯場重鎮。
在鳩摩羅什尊者之前的古譯場時代,譯主多為西域人或從西域來歸順的僑民,他們善於梵語,卻不精漢語,或有通漢文卻不精梵文者,比如道安大師。但道安大師不諳梵文並不影響其譯事,他善於理解精文,智慧過人,校正舊譯諸經的諸多謬誤,且確立了譯經的文體風格。
時光飛逝經年, 精通梵文與漢文的鳩摩羅什尊者讀了道安大師所正諸經,不禁嘆服道安大師所正之文,均能與原典吻合之高明。但羅什尊者心中另有想法,認為佛典要普及一定要漢語化,在地化。
於是羅什尊者主持的逍遙園譯場,其翻譯經文以意寓深遠文辭優美著稱,譯文融合漢、梵文,易於理解。
他一改過去譯文「多滯文格義」、「不與胡本相應」,由直譯改為意譯,辭藻華麗,使誦習佛經者能易於理解接受,成為最普及 最深入人心的譯本。弟子多達三千人,其中聞名者有僧肇、僧叡、道融、道生,稱為「什門四聖」。
羅什尊者於西元413年圓寂,火化後據說舌頭不爛,表示他所翻譯的無誤。譯出了《大品般若經》、《維摩詰經》、《妙法蓮華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大智度論》、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成實論》等著名的大乘經典三十五部兩百九十四卷。
羅什尊者的新經不斷地被翻譯出來,但多以經論二藏為主,律藏欠缺。法顯即慨歎律藏的傳譯不全,一心想往天竺尋求律部梵典,等到機緣成熟時,法顯已然六十六歲,這個年紀的人還有這等長途跋涉只為取經的氣魄,且還成了第一個抵達天竺求得原典者,其可歌可泣的苦行,是雲遊僧西行的永恆典範。
法顯大師曾說:「貧僧獻身於佛教,志在弘法,目的未成,故不宜久留。」他十五年前由長安出發,與長安諸友別離已久,本想去長安。
但是由於北方的政局當時混亂,故一時無法前往,法顯於是南去建康,與佛馱跋陀羅共組一支金陵譯經僧團,創立遙園西明閣譯場,譯場有法顯大師、寶雲、智嚴等沙門參與譯事。譯出的經典,共有六部,六十三卷。
一代代的高僧精勤不懈地翻譯,一部部的經典、一字一句勾劃出天上一道道耀眼的長河。
早期的佛經翻譯,常以一人獨譯,多則二人,相約對譯。後來發展出一套組織嚴密的譯經模式,譯場盛世,高達百人。經過多人之手,反覆勘定,能使字義更貼緊原文,使文采更加斐然。如此譯出的經典,往往影響深遠,千古流芳,所謂「一言三詳,然後著筆,使微言不墜,取信千載也。」
羅什尊者被請至長安城北,渭水之濱的逍遙園,翻譯佛經。羅什能夠背誦許多佛經,嫻熟漢語,對文學具有高度的欣賞力和表達力。所以他翻譯的經文非常流暢,字句精煉,文采斐然。從後秦弘始三年至弘始十一年的八年之間,平均十天一卷的速度進行翻譯,共譯出了七十四部,三百八十四卷佛典。
助手們既精教理,又兼善文辭,各展所長,相得益彰。又有許多西域僧人互相合作,相傳大師譯《十住經》時,因為於理未善,遲疑未能馬上著筆。然後佛陀耶舍來到,共相討論,辭理乃定。
大師的從業弟子號稱有三千,著名者有所謂四聖、八俊、十哲之稱。四聖指道生、僧肇、道融、僧睿。
八俊是在四聖之外加道恒、曇影、慧觀、慧嚴四人,十哲是在八俊之外再加僧略和道標二人。
羅什大師的譯場運作是上午譯經,下午講論,所有的人因此都能獲得大師的講論,借鑒羅什尊者設立譯場的方法,玄奘法師知道須集結各方菁英來到譯場,而非以人數眾多取勝。
自此玄奘法師建立的譯經院成了史上永恆的智慧明光之地。───(未完待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