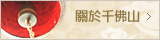- 文:禎佩出處:人物採訪期數:411期2025年7月
老和尚說:「學佛“好不好”不是自己說的,要別人來感覺你是否改變了,別人會看到你的修養、你的表現。」
歸來,風景舊曾諳
受訪/禎佩
整理/編輯部
前言
受訪當日,禎佩一頭清爽短髮,樸素但不失好看的妝扮,語氣溫溫淡淡,蕭颯光潔的臉龐,初看似羞澀與靦腆,打開話閘子之後,卻顯得落落大方。她講話、行事乾淨利落,很少有負面情緒。感於她人生故事一籮框,過往的一切像一團毛線球,她總能在每個線頭中找到敘事的起點,倒帶播映,故事自然出現了落點綰合。此刻生命、生活,流溢著歲月靜好的氛圍,那些過眼雲煙都像眼前一杯茶,散放著滋潤回甘,也是對生命的祝福。
頗富才華的她,因著巧思讓生活多彩,印象深刻的是般若寺茶會聯誼,她會烤可口的蛋糕與大家分享,平常有空就參加活動,探向學習的觸角,這就是她---以平常心迎向無數個明天,積極樂觀的接受生活中現起的一切,體現生命美好的真諦。
她話裡總吐著善意,她說:「人生本來就沒那麼簡單明快,所以少些計較執著,日子比較好過,相信在生活的衝搫當中,那甜點的美味還是有的!」說著,說著,看著她今天帶來的烘焙蛋糕,我忙不迭地嚐了一口。
1、親近千佛山的因緣
禎佩說:
我親近千佛山是妹妹謹蕙拉的緣,我比她先離開澎湖,她倒比我先到千佛山當義工。記得某日我獨自爬高雄大社觀音山,在山上碰到ㄧ群師父,我好奇的問:「請問師父是哪間寺院的?」那時對話的正好是千佛山本願寺的住持──若航法師,他笑著問我:「妳可曾在寺院當義工?歡迎妳來本願寺喔!」
「有啊,謹蕙是我妹妹,她都帶我去般若寺。」「哦!原來同是千佛山!」我們會心一笑。
後來我真的參與其中,到本願寺當義工,一切也覺得順手,在那裡瞭解怎樣當照客,怎樣打點大小雜務,但還是以般若寺為主。最初上崗是過年般若寺的梁皇法會,先前會有零碎的預備工作,譬如點燈、支援香燈打下手,一回生兩回熟,慢慢的盡其所能,也學習了很多。有人問我:「學佛之前跟學佛之後有何不同?我說比較看得開、懂得知足常樂,誇張地說,三百里路之外就可聽到我開朗的笑聲。我看起來樸實、平凡、親切,老菩薩喜歡我,說看到我很舒服,因為我樂於助人,能做的從不依賴別人,臉上總是掛著笑容。
我的人緣不錯,會引領新臉孔來親近三寶,帶他們到千佛山當義工。記得一次,我站在家門口張望,一位女士好像在看房子,她覺得這裡環境清幽,看了看我問:「妳住這裡?這裡會不會淹水?」我說不會。她後來說看我慈眉善目,一派溫柔,想說跟我作鄰居也不錯。後來她也買了這裡的房,往後淹水,我說:「我來買時都沒淹水。」真的!以前都沒淹水,現在竟然淹水,如同人生的轉折。人生是那麼無常,時空環境瞬息即變;就像以前不老,時光暗中偷換,以後漸老。喔,扯遠了,我倆相視而笑,就這麼一笑,拉近了彼此的距離。她發現我常去般若寺當義工也心動了。她叫「錦玲」,以前不知走佛寺,現在她也當起了般若寺的義工,這不可思議的緣,會以不同的方式在時間的網絡上烙印,一切「是因、是緣、是自然」。
老和尚說:「學佛“好不好”不是自己說的,要別人來感覺你是否改變了,別人會看到你的修養、你的表現。」因左鄰右舍看到我學佛學得如此快樂,也想來學佛。我們家開工廠,我做外務,對工人都是將心比心,之前也當過工人,不想以命令的語氣指揮他們,大家叫我大姊。我從不擺架子,逢遇“人事緣境”就往好處想,不希望過於自我──這便是我學佛最大的改變,擁著快樂與滿足,享受生活的每一個當下。
2、對世事的體悟
我常說「佛法真是靈丹妙藥!」有人問:「妳未見過老和尚,但看過老和尚的書,哪句話讓你得到受用?」我回說:「師父曾說『賺的錢不是自己的,而且要把家裡顧好。』所以家庭對我來說就是道場,我想做一個快樂的三寶弟子。記得一次站在般若寺的蓮花池,靜靜的看著蓮花,娉婷的蓮花令我澄心靜慮,彷彿也融入了這片美麗的風景裡。正看得出神,住持惟師父說:「禎佩過來!」從八寶袋拿出一塊糕餅說:「來!我們分著吃。」這一刻,蓮花的美就這樣交織著餅的香甜。
法緣殊勝,能在般若寺向師父學習,在待人處事上常有觀照自心的機會。有一次分東西,師父給我的餅比較不完整,心想:師父是把我當自己人,因為在座的兩位是剛入佛門的訪客。我這人一向服膺「老二哲學」,須完成什麼,只要師父與組長交待一聲,我都會把事情做好,根本不須強出頭。以前我很笨,結婚後在大家族中磨練,更要學著裝笨。可是在職場就要看情況了,小事上不計較、執著,但面對工作須有一份擔當,內心自然要保持清醒、明白。
偶而也有疏忽之時,譬如剛來般若寺遇到梁皇法會,我負責在大殿換電池、點燈、引禮,要把一盞盞的燈放在居士手中。本想最後才去點燈祈福,但典禮組的一位義工說:「禎佩!等一下點燈的人很多,妳現在可以先去點。」誰知又出現不同的聲音:「不是應該先給別人點嗎!我們義工最後才點。」我說:「了解!」所以心思要靈活,於環境、工作還不熟,不要馬上編派理由回嘴,無諍就是戒,謹記著師父的教誨:「多一分修養,少一分煩惱」。
學佛這條路總會閃現驚喜,尤其在佛學班熏習,漸漸蘊育出看世界的不同眼光,就讓佛法滋潤心田,感謝身邊的貴人共譜美好時光,一切從教我珍惜。
我問禎佩:在現實生活中如何運用佛法來解決煩惱? 她說:
師父《禪的語絲》一一七則說:「 每天,每一個時刻,人人都有調整自我的機會;當你面對人與事之時,透視了些什麼?發現了些什麼?無論是正面的或負面的...。」
如果遇到別人言語上的不當,我會選擇關起耳朵,不四處傳是非,不想加進去攪和。我會去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、因緣發展,調整五蘊的受想,避免痛苦的延續,而且眼見耳聞不一定可靠。以前的我愛管閒事,現在不會了!學佛後漸漸改變自我,不喜歡到處說嘴,像含嚼著口香糖。不妨敞開自己,鍛鍊轉念的速度,把佛法運用在生活中,想得清、辨得明,解而行,幸福就潛藏其中。所以學佛讓我對現實世界有更深刻的理解,除了自己也要關照別人的心情。
3、家族親緣
往事已遠,禎佩慢慢的將記憶攏回,她回憶更早的光景,重溯童年濃濃的祖孫情。那是祖母在家修行的時光,清晨四點即起身做早課──
「我是長孫女,都跟祖母睡,所以很早就接觸佛教。那時住三合院,祖母的佛堂充滿了寧靜祥和的氣氛,她靜默穿著海青燒香、敲木魚,小小的我坐在椅上,凝視並聆聽她專注誦經,所以我學佛的因緣蘊含著濃濃的祖孫情。長大後祖母還帶我去澎湖馬公的一間寺院,午後日光煦煦灑落在大殿窗櫺,映照著煙霧縹緲的迷離。幾個信徒或跪或站,虔心默禱。我面對佛像,只求祂給我ㄧ點智慧,其他什麼都不求,因為不能把自己該努力的放著不做,全推給佛菩薩。妙的是晚上竟夢到佛菩薩,教我別四處去亂拜,醒來後彷彿香柱仍存餘溫。
說到尊貴的母教,母親向來溫言柔語,和藹可親,每次回澎湖我擁有一份歸屬感,那個家永遠是我最大的支柱。記憶以來,母親是一位慈悲為懷的觀音,照護家務、呵護小孩,我在媽媽身上學了很多,她總體諒別人,每次回澎湖她都不忘叮囑:「禎佩!妳是人家的媳婦,還是先回夫家看望公婆,等吃了飯若想回娘家再回,我這裡沒關係!也沒這麼多規矩....。」
我十六歲離開澎湖 ,親戚曾帶我去台南元亨寺找出家的姑姑。原來小時候種下的佛法種子,在家庭與事業忙碌下依然盤繞,那道門扉隨時可啟開,不論經過多少時日,最初的斑斕永遠不失。澎湖除了佛緣,也充滿我青少時的記憶:咾咕石堡、曲巷的歲月、老榕與慵懶的貓、風吹、海浪,榕樹下的老人…依稀記得和弟妹穿梭遊玩的情景。我在高雄定居之後,妹妹謹蕙與弟弟也相繼來台灣讀書、工作;那時謹蕙要參加考試,雨災淹水,我還開貨車載她去考場,對他們細心呵護,這也是給父母的一個許諾。幾年光景,他們各自成家立業,迎向新的人生。此外,若有長輩親戚來台,弟妹都會推我去應酬,就此一說「長姐如母」,哈哈,居然口吻一致,算來點滴小事,我就應緣前去招呼。
還有,我感覺女兒是來報恩的,她從小茹素,懂事乖巧,長大後讀醫療工程,某日她正經八百的說:「媽!我允妳ㄧ個醫生。」我傻愣著:「妳想考醫師?」
「我不醫人,只醫機器。」女兒語出幽默、略帶捉狹,能說善道,後來她真的考進醫療,努力工作。我們常一同外出,回來時在門口掏鑰匙時還逗鬧著,鄰居見狀笑說:「妳們母女還能這麼玩?快樂喔!」我與女兒就像好朋友般輕鬆相處,一派和融,女兒總能逗我開心,提供我最新的知識,拉近彼此的距離。
4、騎著“小紅馬”來去自如
訪談結束,午後陽光依然熾亮,問她怎麼來的?她說騎著小紅馬(心愛的紅色摩托車)。「不覺路遠嗎?」
「不會!從高雄般若寺經過岡山、阿蓮就到菩提寺了,路線才40分鐘而已。有一次我還騎到南鯤鯓,再騎到安平,反正都在台南嘛,吹吹風,看看鄉野的繁花綠樹頂有趣。」
「為何不找伴同遊?」
「多麻煩!ㄧ個人遊山玩水多自在,一路看看聽聽,不同的視野與思考可調整自己,眼前遼闊的風景讓人清空思緒、放鬆身心。還有人問我為何感覺這麼豐富?其實我沒有過多的沉溺貪玩,因為綠草、雲空入眼即淡,什麼都不需執著,只是對世界抱著好奇,也因為知道自己要什麼,就能勇敢的走下去。」
感謝豐足的晨光共度,就讓流淌的夢想與故事陪她悠晃而歸,相信在日常的生活氣息裡,必定常有收穫,包括那些一閃一閃的驚奇與喜悅、不期而遇的發生。
我打趣著:「南鯤鯓、安平、岡山到菩提寺,一路驀直去,然後呢?」她回說:「然後?不就回高雄嘛,回“般若寺”那個家,依舊是帶著“平常心”過日子,我還是我呀!」
好個“平常心”!好個“風景依舊”。臨別賦歸,再次見她熟悉的笑容,一如今早初見的伊。但願在菩提道上,她永遠充滿自信,是一匹「識途老馬」,精神開闊,步履灑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