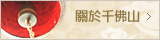- 文:編輯部出處:佛研院園地期數:355期2020年7月
詹教授:我曾向老禪師請益:「世間法無量無邊,佛法如何對待?」 老禪師的回答很扼要:「佛法亦無量無邊!」
佛法與現實之間 佛法與管理學的思考(上)
受訪/詹天賜
採訪/編輯部
前言
佛法三藏十二部閃耀著生命的智慧與光芒,依教如法而行,法身慧命有所增長;管理學可以啟發「永續經營」與「自我的更新」,佛法與管理學各有其機樞,管理學致力於「見樹又見林」,而佛學是不滯留於樹與林,連這兩端都要超越。鑑於現在文明科技顛峰發展,時代不斷輪遞,一切瞬息萬變,問題亦層出不窮,因此將佛法與管理學挹注人生,向著光明而行,這是刻不容緩的事。
佛法談「戒定慧」、「因緣與因果」、「八正道」、「四念處」....等等,具有龐大厥偉的脈絡與架構,詹教授學佛多年,又在管理學的研究也是浸潤有時,加上在交大教學,作育英才、傳承有功,今天雜誌社能請到博學多聞的他來談談「佛法與管理學的思考」,真是與有榮焉!
詹教授曾經在發表的論文──「系統思考與管理教學研究經驗談」中表示:「在國內管理領域從事系統管理方面的研究,是要有勇氣的,由於我先學資管,再學系統,因此進入交大管科系,也是先從事資管方面的教學研究工作,系上成立碩士班、博士班後,再逐步將重心轉到系統管理來....。」以下是本刊編輯與教授就幾個階段分別拋出的略說、介紹。
一、「整體」與「系統思惟」
編:詹教授!今天的採訪題姑且稱為「佛法與管理學的思考」。在未討論之前可否請問詹教授:在親近老禪師的過程當中,有沒有向他請益過什麼問題?
詹教授:我曾向老禪師請益:「世間法無量無邊,佛法如何對待?」
老禪師的回答很扼要:「佛法亦無量無邊!」
管理學是一門綜合學域,包含範圍很廣,從解析的角度,它可分為“人力資源管理”、“財務管理”、“生產管理”、“行銷管理”、“組織與行為”、“研發管理”等。而這些功能管理,與各領域的知識都有關係,例如“組織與行為”的探討要借助社會學、心理學、政治學等學域的知識,“行銷學”在探討消費者行為時也要借助經濟學、心理學等學域的概念,因此要學好管理學,就要充實各相關領域的知識。
從系統的角度,以整體的觀點來看管理學時,牽涉的概念與方法更為廣泛,包含系統觀、系統思維、生命系統、控制系統等。例如在如何設定系統目標時,要考慮系統所處的環境,這些環境包含產業環境、技術環境、政經環境等,科技產業還要特別關注科技產品的進展速度、法律問題等,企業系統可說是一個複雜、動態的系統,是有其研究難度的。目的論雖可簡化探討系統的難度,但在企業目的的探討上,依舊要面臨世界觀、價值觀的內涵,也有其分析上的困難,只是探討這些內涵,在人生界是十分有意義的,也十分有趣。
編:您提到管理學龐大的系統架構,佛法也有自身的系統思惟,老禪師在其《思路》中有說:「生命中的糸統學,以心意識為內涵,以身口意為層次;時間與空間的運作,完成了知識經驗的成果;如是,蓋定生命的價值,寫下生命史實的功過。」
佛法強調價值饒益,著手於「心」的管理;世間法是相對的,它有多少缺失,佛法就有多少絕對性的道理方法與之對應。因此「自我的修養」與「功德跟別人分享」,自利利他是佛法關鍵的課題,誠如老禪師說的「不要以自己的個性去要求別人,要以修養去影響別人。」而佛法的修養無限,思路的開拓也無限,才有八萬四千法門、三藏十二部的弘衍。剛才您說「從管理學的"整體觀"來看,牽涉的內容很龐大,包含生命系統,系統思惟...」,什麼是「系統」?管理學又怎樣看「整體」與「系統」的關係?
詹教授:系統管理是把組織看成是一個系統,也就是看成一個整體系統,而系統有它組成的元件及其超系統。以企業為例,元件就是各部門,超系統就是包含它的產業系統、技術系統、社會系統等。以人為例,各器官是它的元件,而家庭、社會就是它的超系統。
系統可由結構與程序的來探討,由結構來看,系統是由各元件所組成的,大家在簡報上看到的組織圖,就是一個簡要的組織結構圖。管理學在談論「整體」與「部份」 (元件) 時,常引用「瞎子摸象」的例子,來說明整體的主要性質與元件的性質是不同的。以管理者所需要的技能來看,基層 (元件) 最主要的技能是技術,就像大象的鼻子、耳朵各有其功能。中層管理最需要的技能是人性技能 (溝通、協調、激勵、領導等技能),就像大象的各種動作,十分協調;而高階管理最重要的是概念技能,他 (們) 要能具有前瞻力、洞察力,能掌握產業、經濟、技術的脈動,能建立企業的核心能力,以因應未來環境的衝擊;就像象群在面臨乾旱缺水時期,作為領導的母象,具有較充分的經驗,能帶領象群長途跋涉,以找到維生的水源。
再以人體為例,談結構的是解剖學,而談程序的是生理學,後者包含循環系統、呼吸系統、消化系統、泌尿系統、生殖系統、神經系統、內分泌系統、運動系統等,它強調的是程序與功能。至於整體的功能,則強調「綜效」,也就是整合的效果,即所謂「整體大於部份的綜合」、「一加一大於二」等。
編:哲學看「整體」與「部份」是「整體大於部分加起來」,算術是「部份加起來等於整體」。佛法看瞎子摸象這問題,於「整體」與「部份」的思考應該其中都有道,認為:執迷的人看這世界就像瞎子摸象,失之偏頗,因此「宏觀」與「微觀」都不可偏廢。老禪師「蘋果的算術題」中的禪法:「1+1不等於2」,隱喻做人做事要知靈活變通,不能刻舟求劍,僵守著狹窄的思考。請問詹教授管理學怎樣看「瞎子摸象」?能否舉例說明它怎樣成為「集思廣義」的內涵陳說?
詹教授:管理者面對的問題很多,有的是部門的問題,有的是部門互動的問題,也有的是整體的問題,也就是系統與環境互動的問題。一般而言,當系統層次愈高,考慮的層面愈廣,面對的複雜度愈大,若墨守原有的知識領域,就如瞎子摸象一般,會找不到解決問題的頭緒。管理者隨著職位的提升,視野必須要加大,技能要多元化,也就是說管理者需不斷的學習,以充實所需的知識經驗,來因應新職位的挑戰。
「一加一大於二」在學術研究上是十分常見的,例如在博士班「研究專題」的課,集合了許多不同領域的研究生,在研討過後,常激盪出一些想法,這些想法在研討前是大家「沒看出來」或「沒想到」的。也就是說,知識經驗的累積可以透過集思廣義來達成的,而集思廣義的前提是參與者願意分享個人的經驗與心得。
以「系統觀」從事學術論文的研究也一樣,博士生具有專業領域的知識,當他不斷的吸收系統方面的知識與方法後,對問題的看法也就不一樣;而我在吸收他們的專業知識後,也增加了一些知識經驗,在不斷的互動探討過程中,逐步的對問題有了不同角度的認識,從而能夠提出了一些具有原創性的觀點。
有位蕭教授在他進博士班前,具有產業經濟的知識,熟知台灣的汽車產業發展概況,擬深入探討台灣汽車產業的一些問題—例如:「為何台灣汽車產業無法發展出自己的品牌,只能作代工;而汽車零件的外銷,卻有著不錯的成績等。」經過一年不斷的摸索與探討後,逐漸找到了四個關鍵的角色:汽車廠商、政府、技術提供者、消費者行為,這四個角色的互動,影響了台灣汽車產業的發展,而互動的模式也逐步建立。再經過一年的努力,量化的工作也次第完成,論文的撰寫,包含投國際期刊、博士論文也相繼完成。因此,跨領域的研究,相互學習十分關鍵,累積較多的知識經驗,才能作進一步深入的探討。
管理本就是「透過他人完成事情」,因此管理者除了要有足夠的知識與管理技能外,與他人的良好互動,共同面對問題、分析問題、探討問題,也是十分的關鍵。人生的煩惱,屬於個人的部份,可以內求諸己,但屬於群體、組織、社會的部份,則需借助他人,分析探討的難度就會增加了。
就整體而言,有時 1+1也會小於2,這也是十分普遍的現象,例如群體失和,做起事來,諸多不順,綜效便不彰。從學術術語來說,這就是熵,指的是不做功的能量。例如人若是有熱忱,便能發揮他的專長與功能,但若是有心結,被動做事,有能量而不充分發揮,就很可惜了。
編:這麼看來,「整體」與「系統化思惟」有密切的的連結,整體龐大不好掌握,「系統思考」就是要「觀察整體」,進行問題的分析與解決。採用整體與部份的關係圖,解釋千絲萬縷的思考線索,梳理因果關係更糾結的流程。
詹教授:在學術上走系統管理的路,是比較辛苦的,我在「系統思考與管理教學研究經驗談」(系統思惟與管理,第二卷第二期,2-13頁) 這篇文章中,談到了教學研究的歷程。總體來講,從事系統觀、整體觀方面的研究,雖然是管理學界中的「異類」,但研究成果是可觀的。只是因為健康等因素提前退休,否則仍在學術圈中鑽研,便無法及時充實健康方面的知識與經驗,走人生不同的道路了。
二、「表相與本質」的思考
編:剛剛談「刻舟求劍」與「瞎子摸象」,其實離不開「本質思考法」的體現。就像老禪師舉算術蘋果的問題「1+1不等於2」,不能執著、計較,而佛教原本「瞎子摸象」的故事用在管理學竟然是「集思廣義」!可見看問題不能只看現象,亦即老禪師常說的:「“法”在哪裡?」那就要透過現象,看到它背後的本質與意境,主動做到未雨綢繆。佛法幫助我們認識瞭解問題,甚至平常疏忽不注意的、想不到的細節。以老禪師說的:一個完整的佛法包括「體、用、相、境」,這四者缺一不可。詹教授能不能再談談「表相與本質」的思考,我覺得本質應是更跳脫、深入的發現吧!
詹教授:“本質”的問題需要窮究,屬於哲學上的難題,“表相”則較易探討。例如華而不實的現象是十分常見的,像申請學校的甄試資料,可靠性有時是值得懷疑的。備審資料多數是有備而來,做得不錯,有一次有位老師覺得書審資料的格式做得特別好,就隨口問道:「你這資料是怎麼做出來的?」學生的回答竟然是:「學校提供的軟體做出來的。」又有一次,有位老師看到學生的資歷十分豐富,便問道:「你們班長是怎麼選的?」學生的回答是:「我們班長一個學期選四次!」經過多次的甄試經驗,老師們對書審資料的可靠度產生了諸多的質疑,因此比較相信口試。實際上,書審資料繁多,老師們並沒有足夠的時間逐份仔細的看,因此,書審資料的首頁,是重中之重,一定要能簡單扼要的陳述重點,老師們才會有興趣仔細的翻閱,以找出想要的學生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口試也會有城鄉差異,城市來的學生比較伶牙利齒,應對流利;而鄉下來的學生則普遍不善表達,有的端坐在對面,顯得有點緊張,我們很想問些較輕鬆的問題,引發他的回答,但效果不好,很難給予好成績。
用系統觀看問題,與傳統的解析方法是不一樣的。「解析法」,是逐步分解法,系統有問題,看元件,看那些元件出問題,然後逐一解決。例如生病了依科別來看,若是同時有內科、皮膚科的問題,則分別到這兩科門診看,住院則可會診。「系統觀」則不然,是整體的看,就像中醫,依症候探究是五臟六腑的問題,還是經絡或體表的問題,是寒還是熱,是濕還是燥等,還要探究病機,探討病是如何發展而成的。
用系統觀來探討問題,重點常在於元件的互動及系統與環境的互動上,這種研究有時是十分困難的,因為面對的常是互為因果、環環相扣的問題,其複雜性難以掌控。就像現代許多常見的慢性病,原因多半不詳,難以探討。例如高血壓,多數的高血壓屬原發性的,原因不詳;但是造成高血壓的原因不是不能探討,只是十分複雜,不好探討。不良的生活方式、遺傳因素等都可能造成高血壓,只是這些造成高血壓的危險因素,如何透過互動過程形成的,則難以作有系統的研究。怎樣的飲食習慣、運動習慣、體質、吸煙習慣等這些多元因素,如何逐步相互影響形成高血壓,看似簡單,其實在研究上很難下手,實証上更難進行。
由此可知,森羅萬象,有時過於複雜,難以探討,表象能解,就能符合人的需要,因此,高血壓只要能用藥控制,不必去追問原因,就成了常態,若要追究,便成了沒完沒了的事。中醫除了學理之外,更依賴經驗、體悟、直覺,難以傳承,是因為複雜度難以掌控,難以解說清楚。歸結到氣血、經絡、五臟六腑、情志、邪氣等,以陰陽五行等概念,來詮釋複雜的病理,探究人的身心互動,已是古人能留傳下來的心血結晶。
三、「已知」與「未知」的思考
編:管理學會探究你目前“已知”的現況,加上對“未來”目標的訂定,可否聊一下這方面?
詹教授:用“系統觀”來看問題,要了解現有狀態 (現況)、提出期望狀態 (目標)、及由現有狀態達到期望狀態的方法 (策略)。對現況的瞭解,需要知識經驗,對期望狀態的設定,也需要知識經驗,策略的提出,同樣需要足夠的知識經驗。例如身體的現況,西醫採用身體檢查、病歷追蹤、問診等方式來了解健康狀態,中醫則以四診來探究身心狀態,都是了解現有狀態的方法。至於企業的現況,可由企業內部來評估,包含「財務、產能、人力、研發能力」等各方面的評估,也可由企管顧問來評估,再綜合來看。
至於期望狀態,與現有狀態有關,也與環境有關,更與如何達成所期望的狀態有關。例如少子化,對整個經濟、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;又如科技的發展,也是影響十分重大。目標的擬定,要考慮到未來環境的變化,要及早因應,早日建立能因應環境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,例如各道場建立網站,提供電子化期刊等,都是因應環境的方法。對非營利組織而言,訂定目標最重要的仍是價值觀,例如各宗教都有其不同的世界觀、人生觀、與價值觀,因此在訂定目標上,理想是個很好的參考。有系統學者提出理想是一個無法達成的目標,但它可逐步的趨近,因此可以分階段來訂定短、中、長期的目標,以不斷邁向遙不可及的理想。
編:所以談“分析問題”,有種種的「已知與未知」,像鑰匙掉在黑暗的地方,你在明亮的地方找,也找不到。“明亮”比喻你用你已知的經驗知識去找,可是時空已變了,你卻拘於過往的所知,怎麼能解決問題?這無異是一種無明。誠如您所言,這次的肺疫,原因不容易馬上找到,因為有太多的隱藏性。
佛法談智慧還涉及到「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」,層層提昇,求得問題的化解,乃至離苦得樂,達到生命最究竟的解脫,這才是生命極至的最高管理。不知管理學的分析方法是怎樣的?
詹教授:“解析法”仍是現代科學的主流,看問題、解問題,邏輯清晰、推論清楚,在現實世界可以驗証。但解析法也逐步碰到了瓶頸,那就是在複雜與動態的情境下,對整體的所知仍然有限。以這次的新冠病毒為例,對於確診的病患,只能靠自身的免疫能力來對抗病毒;當病毒入侵肺臟,造成呼吸困難時,就只好依賴呼吸器來維生,再靠自身的免疫力來抗病。這時,講究整體的中醫,它的功能就出現了,不論何種未知病毒,都可以很快的找到適當的中藥對治,配合針灸,就可以取得不錯的療效。而西藥一時之間,並無對抗病毒的特效藥,疫苗的研發也費時費力,而且要考慮病毒變異的問題。其實疫苗的概念與方法,也來自中醫的人逗術,傳入西方後,才逐步改進成疫苗。
由此可知,“解析法”雖為主流方法,但仍有其侷限,就像著名的管理哲學家 Churchman 所言,現代科學只是初階科學,我們對現實世界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。用“系統方法”、“整體觀”來看問題,可以看到「不同的世界」,但它的嚴謹性、可驗証性讓人存疑,就像中醫講究天人之學,談精氣、陰陽、五行,在醫學界是受人質疑的。因此,如何融合中西醫這兩種醫學,仍是個有待探討、深究的主題。
利用系統方法來做管理方面的論文,也面臨一樣的處境,面對諸多教授的質疑,使得研究生以系統方法來進行研究,變得十分的艱難。因此,在校期間,我逐步放棄了碩士生的研究課題,改收博士生攻堅,經過多年的努力,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,才獲得同事們的肯定,不再以異樣眼光看待我們這個研究室。
編:有的歐美哲學思想一路分析下去,最後無法跳脫現象的第一因,就推到最後的“因”是神,認為只有全能的神,才有辦法解決最終極生命的問題。這就牽涉到問題與答案的尋求;佛法的分析問題不是只找答案而已,它是一種「運用思想,發揮智慧」的工夫,不時興「背著竹筏子過河」!過了河就要放下竹筏子。佛法遇到問題當然要分析、認識,但是最後會回頭返照自己,問「為什麼?」 「跟自己有什麼關係?」
詹教授:理性論的源頭是非理性的,因此只能將第一因歸諸於神,而要証明上帝的存在。以歐氏幾何為例,它有21條公設,這些推論依據的公設如何而來?只能歸之於「自明」、「直覺」。例如兩點決定一直線,來自每個人的直覺,它是人生來具有的本能,故只能歸諸於神,歸諸於天。就像一位哲學家所說的,人以科學方法來探討宗教問題,是難解的,生前死後是個未知世界,人的能知是否能及,人又能了解自己多少?「認識你自己」,從古希臘到現在,仍然是個探究不盡、認識不完的難題。(未完待續)